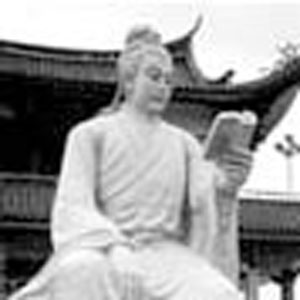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从《西江月》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鹊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鹊儿被惊醒了;而鹊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特别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
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
前四句就是单纯的抒写当时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下阕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阕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成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见”,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欣,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稻花香中以至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这首诗,寓新语于古风,写来浅白轻灵而富于情韵。诗的首句先点染秋日湘江的景色。秋日湘江,无风无浪,放眼望去,更显得江面开阔。七个字中出现两个“水”字,这是诗词中常见的“同字”手法。前一个“湘水”,点明送行的地点,后一个“秋水”,点明时令正是使离人善感的秋天,笔意轻捷而富变化。联系全诗送别的情境来理解,秋江的无潮正反衬出诗人心潮难平;秋江的开阔正反照出诗人心情的愁苦抑郁。次句“湘中月落行人发”,具体交代送行的时间,是玉兔已沉、晨光熹微的黎明时分。第一句着重写空间,第二句着重写时间,而且,次句开始的“湘中”和首句开始的“湘水”,“湘”字重复,不仅加浓了地方色彩的渲染,也增强了音韵的回环往复之美。
流利自然,是乐府诗的特色之一,而在句式上用了长短句,是获得流利自然的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首诗的后半首就是这样。“送人发,送人归”,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紧承第二句,前后连用三个“人”字,两个“送”字,两个“发”字,加强了诗的行云流水回旋复沓的旋律,而加上“发”与“归”的渐行渐远的进层描写,就对送别的意绪作了回环往复的充分渲染。如果说,前面两个七字句弹奏的还是平和舒缓的曲调,那么,“送人发,送人归”,则为变奏之声,急管繁弦,就“凄凄不似向前声”了。最后一句是写斯人已去的情景。“白蘋茫茫”是江上所见,回应开篇对秋江的描给,诗人伫立江边遥望征帆远去的伤感情态,见于言外;“鹧鸪飞”是写江边所闻,和茫茫的白蘋动静互映,那鹧鸪的“行不得也,哥哥”的啼鸣,仿佛更深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和怅惘。这种以景结情的落句,更给读者以无穷的意味。
这首诗描述湘江畔送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无比惆怅的思想感情。全诗语言浅白而情韵丰富。
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诗的首句正是袭用这句俗语的语意。“才近”二字,扣题目的“八月十二”,只差三天,便是中秋,真称得上“近”了。本来每月的望日,月亮都是光明的,而这句俗语突出的是“中秋”,重点在“分外”。分外者,特别之意也,即较之其他月份更要清亮一点。八月十二,虽还未到中秋,但却接近中秋;虽未达到“分外”,却也是“已清”了。这已初步道出了题意。
第二句,进一步写“望”。诗人所望见的是“鸦青幕挂一团冰”。仰望高空,俨如帷幕,色比鸦青,倍觉淡雅。在这淡雅的帷幕之上,悬挂着一轮明月,色泽的优雅、美丽,颇能引人入胜。还不止此,在这里诗人不说“月”而说“一团冰”。团者,圆也;而冰的内涵首先是凉其次是亮,再次是白,这较之“一轮月”不仅更为形象,而且创造出一个既优美又冷清,既光明而又优雅的境界。它不仅给与读者以美的享受,而且能给人以情操的陶冶。
第三句在全诗中是一个转折,是第二句到第四句的一个过渡。“忽然觉得今宵月”,通俗易懂,简直就是一句白话。这种语言,新鲜活泼,是诚斋诗的特点之一。
第四句则说明“忽然觉得”的内容,也就是对“今宵月”的一个遐想。月是历代诗人最喜欢歌咏的景物之一。在诗人的笔下,月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而他们由月所引起的遐想,也是各不相同的。而诗人能独辟蹊径,别有所想,出人意表。诗人想的是这个月亮“元不粘天独自行”。“元”即“原”字,意思的“原来月亮并不是粘在天上而是独自行走的”。夜空片云全无,一轮明月高悬,似乎无所附丽,独自运行。设想新奇,月夜晴空的境界全出。
这首小诗,既创造出优美的境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又出以新奇的遐想,启迪着读者的思路;而那种通俗的语言,虽然传统的诗家,视为“鄙俗”,却使读者感到新鲜活泼。
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