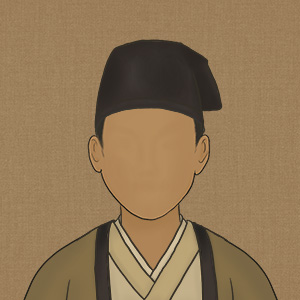因友人陆澧邀诗人到山中居处饮酒小叙,诗人遂赋此诗作答,表示欣然愿往。全诗以酒为引子,写得颇具特色。
前两句:“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松叶”清香,可以作为酿酒的作料,引出下文之“山路”。“春来”二字,点明时间。次句采用问句的形式,似问非问,略显诙谐,直接道来,足见诗人与友人的浓浓真情。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之三曾云:“明珠可贵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酒最能代表人间的真情,饮酒时最容易沟通与别人的感情,作者开篇即选取这种极为平常却又极富深情的事物,随意而问,显得浓情依依,轻快自然。
后两句“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山路”二字,照应前面“松叶”。为了喝朋友的松叶酒,更为了与朋友饮酒倾谈,诗人表示即使山路遥远崎岖,也要拜访友人,朋友情深,于此可见一斑。而结句语意更进一层。由春来可知,此时已是春天,山中已然冰融雪化,这里诗人作了一个假设:即使积雪满地,也要前往拜访。此句既是说诗人自己,又似告诉友人,应该如此。结句看似平淡,实则蕴涵丰富。
这首绝句体小诗,短小而质朴,亲切而自然。诗中用语极为平实,几乎就是口头语,然而从容写来,淡而有味,语浅情深,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有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子,这种风格又被后来的王维、孟浩然等发扬光大,形成山水田园一派,张九龄不愧为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
诗题为《客夜》而通篇不见“夜”字,但又全是客夜之景,客夜之情,读之真感有高处着笔,不落言筌之妙。全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擎,意境清幽,含蓄蕴籍,耐人寻味。
首联“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提笔入题,笼罩全篇。“何曾”“不肯”四字尤为历来评注家们所赞赏。这四字诗人在别处虽曾用过(《复愁十二首》“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但用在此处却显得特别精警。它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睡不着还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金圣叹《杜诗解》)的情态。王嗣奭赞此四字“用得精神”即是说展现了形象,传出了神采。葛立方也说:“含蓄甚佳。”(《韵语阳秋》)这里所谓的“含蓄”也正是就它表现的形象意蕴的深度而言。
颔领“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紧承首句“客睡何曾著”而来。从文字上看,好像只写的是月影江声,秋夜之景,但实际显现的正是客愁不寐之情,不过诗人用的是衬映手法,以景寓情罢了。“高枕”是杜甫习用词语,集中凡十见,用于律诗对句共八处,其中六个高字均“死字活用”(参见施鸿保《读杜诗说》),用语法术语说即是“形容词用作动词”。梓州四周多山,江水从远处山间流来,夜静之时在枕上听之,觉其声来自比枕高之处。
月影由东窗渐移西窗,分明是后半夜的光景,故说“残月影”。月儿筛过窗帘,光影洒地,对无忧的人说来正是秋夜美景,但对今夜愁苦熬煎,竟夕不寐的诗人来说就倍增烦恼了,只好斜倚着让自己轻松自适些。殊知,那远处的江声又听得更清,扰人愁烦,何况这江声又是远江之声,更把诗人的愁绪引向“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的成都。新营的草堂,留居的妻儿,都是难堪的系念,而“家远传书目,秋来为客情”(《悲秋》)则更使情怀悲怆了。诗人不直接着墨于竟夕不寐的愁苦而以残月江声之景出之,真是“文外曲致”,含味无穷。
严武离蜀,杜甫失掉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梓州是严武领东川节度使时的旧地,那里有他的旧部、僚属,借严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生活资助,这次诗人去梓州除了避乱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因素。从诗人这时期写的许多投寄,奉赠和参加宴饮的诗来看,不难得到证实。他几乎向当时在梓州稍占势要的人(如李梓州、杨梓州,严二别驾以及留后章彝等)都委婉地表示过冀求资助之意,但得到的不过是几次应酬宴请和临时的少数周济罢了。因而诗人不断发出“巴蜀愁谁语”(《游子》),“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的孤独与绝望的悲叹。他将离梓州时写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句,可算诗人这一时期凄惶无依生活的总写照,也是颈联“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最好注脚。从结构上看,颈联二句正是遥接首联“秋天不肯明”句而来的,它具体地倾诉出“不肯明”的烦怨之情的根由。
尾联“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老妻催归,使诗人更陷入了欲归不能的焦灼之中,如何回答老妻,千愁万绪,苦衷难述。杜甫在这里是说:“老妻啊,你是应当理解我不能回家苦衷的,为什么写这样几页长信催我回家呢?”诗人不在结尾处用重笔再写自己不眠的痛苦而拓开一笔写老妻应理解我不能归家的苦衷,写得含蓄,说得真切,无限酸哀涌而不吐,令人不忍卒读。从全诗结构看,这两句不但是全诗感情发抒的高潮,也是首联“何曾著”“不肯明”的归穴。层次起伏,首尾一贯,曲尽章法变幻之妙。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