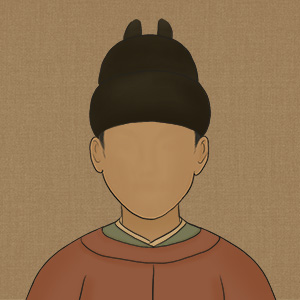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全词情词并胜,神韵悠然,层层深入揭示了抒情女主人公心中无限愁情。
词人首先写道:“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闺”指过去年轻女子居住的内室。“柔”有作“愁”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独处在深院闺房中,心中总是积郁了千丝万缕的愁绪。开篇就以抒情笔调切入主题,再现了词人独守深闺,孤单寂寞,思念亲人,愁情不绝,柔肠寸断,叫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状。“柔肠一寸”就是“愁千缕”,由此可见词人寂寞愁苦、深情绵长、思念之情无可排遣的程度已经到了极致。
接着写道:“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崔花雨”这里指崔花调落的雨。这是环境描写,意在烘托主人公忧愁的心境。一个“惜”字表明了词人对“春春去”的情感。接着又是“几点催花雨”,真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原本令人怜惜且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春天却走了,可是,“屋漏偏雨”,这里,春去而偏又下起了摧残鲜花的暮春雨。可见,词人惜春中自然也包含着怜惜青春年华的心理。
接着下片写伤别,抒写词人对丈夫强烈的思念和盼归之情。
词人写道:“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无情绪”就是心怀抑郁惆怅,没有兴趣。“独处深闺”的词人,心头总觉是“寂寞”,更是“柔肠一寸愁千缕”。词人深感寂寞,只好走到闺房外面,看看外面的风景,也好排遣心中的忧烦愁思。可是“倚遍栏杆”,极目远望,终究还是没有好心绪,真有“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温庭筠《望江南》)的感受。词人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他乡,望不见的,可是心思又放不下,而词人“倚遍栏干”不但不见丈夫,甚至还不知道“人何处”。
结尾处,遥问“人何处”,点明凭阑远望的目的,同时也暗示了“柔肠一寸愁千缕”、“祇是无情绪”的根本原因。这里,词人巧妙地安排了一个有问无答的布局,却转笔追随着女子的视线去描绘那望不到尽头的萋萋芳草,正顺着良人归来时所必经的道路蔓延开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然而望到尽头,唯见“连天芳草”,不见良人踪影。
这首词上片写伤春之情,下片写伤别之情。伤春、伤别,融为柔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刻画出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结尾“望断”二字写尽盼归不能的愁苦,此时感情已积聚至最高峰,全词达到高潮。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此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往“访”,重在写景,景色优美;末两句写“不遇”,重在抒情,情致婉转。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首联是说,隐隐的犬吠声夹杂在淙淙的流水声中,桃花带着几点露珠。
诗的开头两句展现出一派桃源景象。首句写所闻,泉水淙淙,犬吠隐隐;次句写所见,桃花带露,浓艳耀目。诗人正是缘溪而行,穿林进山的。这是入山的第一程。宜人景色,使人流连忘返,且让人想到道士居住此中,正如处世外桃源,超尘拔俗。第二句中“带露浓”三个字,除了为桃花增色外,还点出了入山的时间是早晨,与下一联中的“溪午”相映照。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颔联是说,树林深处,常见到麋鹿出没。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
颔联写的是你是诗人进山的第二程。诗人在林间小道上行走,常常见到出没的麋鹿;林深路长,来到溪边时,已是正午,是道院该打钟的时候了,却听不到钟声。这两句极写山中之幽静,暗示道士已经外出。鹿性喜静,常在林木深处活动。既然时见鹿,可见其幽静。正午时分,钟声杳然,唯有溪声清晰可闻,这就更显出周围的宁静。环境清幽,原是方外本色,与首联所写的桃源景象正好相衔接。这两句景语又含蓄的叙事:以“时见鹿”反衬“不见人”;以“不闻钟”暗示道院无人。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颈联是说,绿色的野竹划破了青色的云气,白色的瀑布高挂在碧绿的山峰。
颈联写的是诗人进山的第三程。从上一联“不闻钟”,可以想见诗人距离道院尚有一段距离。这一联写来到道院前所见的情景——道士不在,唯见融入清苍山色的绿竹与挂上碧峰的飞瀑而已。诗人用笔巧妙而细腻:“野竹分青霭”用了一个“分”字,用来描画野竹、青霭两种近似的色调汇成一片绿色;“飞泉挂碧峰”用一个“挂”字,显示白色飞泉与青碧山峰相映成趣。显然由于道士不在,诗人百无聊赖,才游目四顾,细细品味起眼前的景色来。所以,这两句写景,即可以看出道远的一片净土的淡泊与高洁,又可以体会到诗人造访不遇,怅然若失的心情。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尾联是说,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我不由自主的靠着几株古松犯愁。
结尾两句,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从侧面写出“不遇”的惆怅,用笔略带迂回,感情亦随势流转,久久不绝。
此作的构思并不复杂,它写诗人的所闻所见,都是为了突出访道士不遇的主题。全诗辞句平易自然,纯用白描,景美情深。当然,并不是说李白这首诗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后期比较成熟的诗作,都写得十分洒脱、酣畅、飘逸、雄浑,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豪气。而他这首诗,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浓郁。这说明此作还带有他早期作品的痕迹。
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
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