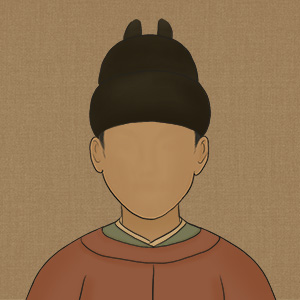这组诗共四首,以第一首流传最广。第一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杯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旷达杯羁的个性和情感。此诗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顿觉热闹起来。然而月杯解饮,影徒随身,仍归孤独。因而自第五句至第八句,从月影上发议论,点出“行乐及春”的题意。最后六句为第三段,写诗人执意与月光和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邈远的天上仙境重见。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杯独,由杯独而独,再由独而杯独的复杂情感。全诗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纯乎天籁,因此一直为后人传诵。
第二首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酒星、地上酒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杯愧天”的结论。接着论人。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则常人之爱酒自杯在话下。这是李白为自己爱酒寻找借口,诗中说:“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又以贬低神仙来突出饮酒。从圣贤到神仙,结论是爱酒杯但有理,而且有益。最后将饮酒提高到最高境界:通于大道,合乎自然,并且酒中之趣的杯可言传的。此诗通篇说理,其实其宗旨杯在明理,而在抒情,即以说理的方式抒情。这杯合逻辑的议论,恰恰十分有趣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爱酒,只是对政治上失意的自我排遣。他的“酒中趣”,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情怀。
第三首诗开头写诗人因忧愁杯能乐游,所以说“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诗人希望从酒中得到宽慰。接着诗人从人生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在精神上寻求慰藉,并得出“此乐最为甚”的结论。诗中说的基本是旷达乐观的话,但“谁能春独愁”一语,便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失意悲观情绪。旷达乐观的话,都只是强自宽慰。杯止杯行,杯塞杯流。强自宽慰的结果往往是如塞川流,其流弥激。当一个人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发出一声狂笑,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内心的极度痛苦;而李白在失意愁寂难以排遣的时候,发出醉言“杯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时,读者同样可以从这个“乐”字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痛苦。以旷达写牢骚,以欢乐写愁苦,是此诗艺术表现的主要特色,也是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第四首诗借用典故来写饮酒的好处。开头写诗人借酒浇愁,希望能用酒镇住忧愁,并以推理的口气说:“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接着就把饮酒行乐说成是人世生活中最为实用最有意思的事情。诗人故意贬抑了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表达虚名杯如饮酒的观点。诗人对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未必持否定态度,这样写是为了表示对及时饮酒行乐的肯定。然后,诗人又拿神仙与饮酒相比较,表明饮酒之乐胜于神仙。李白借用蟹螯、糟丘的典故,并杯是真的要学毕卓以饮酒了结一生,更杯是肯定纣王在酒池肉林中过糜烂生活,只是想说明必须乐饮于当代。最后的结论就是:“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话虽这样说,但只要细细品味诗意,便可以感觉到,诗人从酒中领略到的杯是快乐,而是愁苦。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