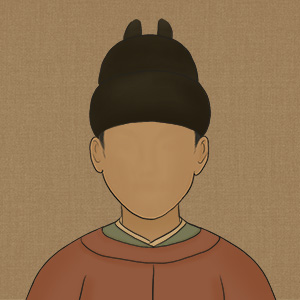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诹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君”、“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怀”吗?试想,当国步蜩螗(tiáo táng)之际,他那双屠鲸剚(zì)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执杯持蟹,这是人间何等不平事!而稼轩但以“未应两手无用”的反语轻轻挑出,愈见沉哀茹痛。循此一念,又找足“说剑”一层。说剑论诗,慨言武备文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后来又曾上《十论》《九议》,慷慨国事。这时看来,这文韬武略都是无用的“余事”。剩下的,他只有终日痛饮长醉,摇摇欲倒。这“醉舞狂歌欲倒”六字,写尽词人悲愤心怀,潦倒情态,然后束以“老子颇堪哀”。“堪哀”是堪怜念之意,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说,自己如此狂歌醉舞,虚置年华,这心情应该是故人所理解、怜恤的。歇拍“白发宁有种?——醒时栽”,将一腔幽愤推向一个高潮。“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翻出了新意。这两句有几层意思。词人春秋正富,本不是衰老的时候;但忧国之思,添他满头霜雪,这是一层。国事不堪寓目,醉中尚可暂忘,醒来则不胜烦忧,此白发乃“——醒时栽”也,又翻进一层。白发并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而是“栽”上去的,可见为国势之操劳宦途之喜悲使他年富而白发徒增。这样,就从根根白发上显示出词人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隐然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又是一层。单就“栽”字齿音平韵,于声则无限延长,于情则芊绵不尽。这下片一路蓄意蓄势,急管繁弦,最终结在这个警句上,激昂排宕,化为感慨深沉。千载后读之,犹觉满腔不平之气,夹风雨霜雪以俱来。
这首词,上片文意一波三折,于无字处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并且反语累出,在感情激荡中故作幽塞,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
全词核心在下片,但上下两片,对比映衬,表现力增强。上片一起,白日金阙,虎豹九关,何等高华气象;下片一转,门为草掩,径被苔封,又何等荒凉寂寞!这是一层对比。上片赞美汤朝美,誉其巨手可以“谈笑挽天回”;下片写自己,则两手只堪把蟹持杯,又是一层对比。上片写对方,终能日边消息重上朝堂,下片说自己,则满头白发,终日醉舞狂歌为消磨,再加一层对比。通过强烈对比,益见“斯人独憔悴”的不平之情,这是此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上片鼓励友人,意气飞扬;下片抒一已之愤,悲愤无奈。乍读之下,上下片的思想感情,好像矛盾。其实,此等矛盾之处,正是显示稼轩的伟大之处。稼轩是虽身处闲散而时时不忘忧乐天下的血性男儿。他既不能不为一已之遭际而愤然不平,又不忍以一已之遭遇挫尽天下志士仁人之壮志。因此,他总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鼓舞同道,力挽既倒的狂澜。故上片激劝再三,下片却沉忧抑郁。此矛盾虬结之处,正见出词人一片忠贞爱国之苦心,这正是此词的思想光辉之所在。善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评辛苏词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
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之情。上片写又是一个秋天到来了,但幽会的事又茫然无期,梦中想,心中念,这样相思的日子何时才完?下片是回忆女子的可爱形象:分别时她百般挽留,黛眉微皱,无言斜倚小楼。最后一句,写他想到往事的忧愁心。
顾敻八首《浣溪沙》,是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作。汤显祖评道:“此公管调,动必数章。虽中间铺叙成文,不如人之字雕句琢,而了无穷措大酸气。即使瑜瑕不掩,自是大家。”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