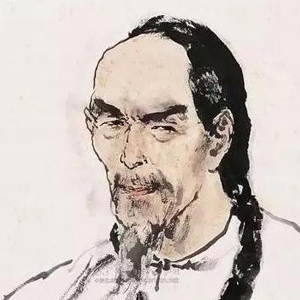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