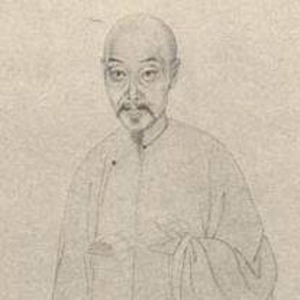黄山有“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石柱峰、吴蓉峰、莲花峰,均高耸峭拔。直刺青天,形如蓬荷。王琦在解释前两句诗时说:“诗意则谓黄山三十二峰曲口莲花,丹崖夹峙中,植立若柱然,其顶之圆平者如菡萏之未舒,其项之开放者,如关蓉之己秀。未尝专指三峰而言也”
诗人自叙曾游黄山,描写其高峻神秀,有神仙遗踪。 黄山的朱砂泉,自朱砂峰流来,酌饮甘芳可口,浴洗令人心境清廓。气爽体舒。自己来到黄山时,有仙乐呜奏,温处士整理仙车相迎。以后我还会时常来访问,踏着彩虹化成的石桥,拜访温处士。
诗人以丰宫的想像、生动的笔触描绘出黄山壮丽多姿的景象;点出众降、练玉处、丹沙井,使人获得非常亲切的美感。
诗人凭借他“伊昔升绝顶”,游览黄山所得到的印象,根据所送的朋友的“处士”身份及其归居之地,驰骋想象和联想,运用有关的神话传说,创作出了这篇具右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前八句正面写黄山,描写它高峡、秀丽,是神仙修炼之地,为写送温处士归山养真修造作为铺垫。 以下十四句从“送”字着笔,是全诗的主旨,中分数层;先写与温处士相遇;次写温处士是游五岳归来,归休黄山白鹅旧居,并希望他在归休之地得道成仙,以引渡自己;再次,“去去”四勺,是写同温处士分手时道剔的话,想象他在途中的经历和将要见到的景象;最后两句写他日相访,表达了诗人对温处士的感情。诗中表现出一种飘然欲仙的浪漫主义色彩。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首联“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新来百感并。”诗人说自己滞留燕京四年,虚耗了精力,空度了年华,尝遍了酸甜苦辣,时逢寒秋,更是百感交集,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书剑”指代文士生涯。以书耀文,以剑显武,是古代儒生本色,是诗人的骄傲。“滞”是不通不畅之意,说明命运多艰,仕途蹇涩。此联上句突出诗人形象,下句“更”字使诗意推进一层,将感情强化,引出“百感”。秋来更增百感,源于“宋玉悲秋”。宋玉《九辩》开头就高唱“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后,它就引发了许多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联想,也成为诗歌创作的触媒。
颔联“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无处访荆卿。”承接上文“百感并”,写其所感。诗人在秋色触目,忧愁苦闷,百感交集之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古人,一个是郭隗,一个是荆轲,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战国策》、《史记》均有燕昭王礼聘郭隗的记载。《史记·燕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隗改筑宫而事之。”《文选》李善注还载有燕昭王于易水边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的故事。两千年来,燕昭王成为礼贤下士的代表人物,郭隗成为文人学子羡慕向往的榜样。
荆轲亦曾受燕太子丹特殊礼遇,同时他还有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而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卿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今云“市中无处访荆卿”,即伤心知己无从寻觅,又隐指像荆轲那样的际遇今己难逢。怀念郭隗,寻访荆卿,表明诗人企盼受到当权者的尊重和厚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英主难逢,古贤远逝,徒令寒士唏嘘感喟而已。两句用典,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其悲秋之情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颈联“浮云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徵声。”放眼远望,万里浮云呈现一片灰黯颜色。顷耳细听,飒飒秋风里传来千年回响的变徵悲音。上联主要是怀古,此联转入了伤今。诗句展现出北国秋色的壮阔景象,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片“伤心”颜色,他听到的却是一种“变徵”哀声。变徵声:变徵为古音阶之一。古人把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又有变宫、变徵二声。变徵音色凄凉,宜于悲歌。“变徵声”与上联“访荆卿”照应。诗人在秋风中仿佛听到了变徵之声,一方面寄托对荆轲的向往和怀念之情,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心境的悲凉。旅京无托,志士失意,不免感到万物同悲,此融情入景也。
尾联“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此尾联收束全篇。京都四年,怀才不遇,知己难寻,在萧飒秋风中,百感交集,憋闷郁结,欲以长歌排遣,却又意兴索然,心情颓丧,只好寻找身份低贱的仆夫隶役共话生平,一诉衷肠了。驺卒:官府服贱役的仆隶。南朝梁人谢几卿曾于闹市与驺卒对饮,为放纵不羁之士所激赏。作者此语既有失意于上层社会,欲到平民中寻觅知己的想法,又有放纵情怀,不计穷通得失的意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前面两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联徒然收回,强自压抑,另辟通途,便产生了沉郁顿挫、纵放自如、悠然意远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