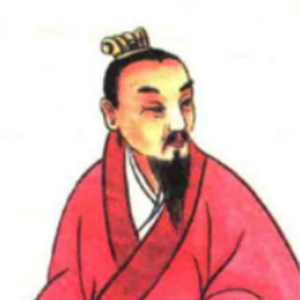这首词,由于作者带着悲壮激烈的心情来写,所以很有气魄,从一开始的景色描写,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写得气势磅礴、感情豪放、情绪激荡。下半片,写世事巨大的变迁,沧海桑田,面貌全非。
沽酒汀边,一身孤零。夜雨傍沱,又兼涛声,其势磅礴。“接着“记当年”以下,连续用典,历数风流人物、兴亡旧事,直至上片收煞,一气奔注,略无滞碍,托兴高远。作者描绘这些历史事件,写得深刻入微,如:“阿童东下”中用“东下”来形容晋王浚进军的气势, “佛狸深入”中用“深入”来说明进军的程度和梁武帝轻敌,用“萧郎裙厩"来比喻他华而不实,最后被围困而死。“笑风流”句,说的是谢玄的北府兵晓勇善战,将领们亦好谈兵法。“笑”字微妙,不能简单理解成讥笑,而应当理解为:当年晓勇的北府兵以及好谈兵的将领们如今何在?此处“风流”有豪爽、粗犷的意思。上片多用典实,却自然浑成,并不涩滞。但每个典故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内涵丰富。如:“阿童东下”,“佛狸深入”,它们各含一个具体,生动,场面壮阔,战斗酷烈的故事。又如:“萧郎裙屐偏轻敌’’,内含了梁武帝被困的故事,指出了华而不实的少年贻误国事。
换头转人即景抚今。“人事改,寒云白”句极言人世沧桑变幻,历代兴亡如白云须臾变苍狗,都只是瞬息间的事。其中词中风景描绘,起了很大的衬托作用。如:“听夜雨、江声千尺。’’又如:“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以落日残照古战场和西风吹进王侯家来显示时代的变迁,且”西风吹尽王侯宅“,意同刘禹锡《乌衣巷》诗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石头城中东晋王侯的住宅如今也不复存在了。最后, ”任黄芦、苦竹打寒潮,渔樵笛“"描绘昔日的战场,已一片冷寂、空旷、残败的景象。只剩下让后人凭吊的遗迹。写黄芦苦竹抽打着红潮,是突出风,江风飒飒,不知渔夫还是樵子在吹着笛子,构成了凄苦幽怨的交响。全词高旷沉郁,苍茫无尽,确有东坡风致。
作者其实是在影射明末清初的镇江战事镇江的失陷与守将杨文骢的当生意气,骄傲轻敌脱不了干系。将大清军用灯笼火把伪饰起来的空筏看作是满载敌兵的战船,正当杨文骢为发炮击沉了清军的空筏而沾沽自喜时,清军主力已在大雾的笼罩下发动偷袭,杨文骢的狼狈与尴尬遂成为那场灾难的终点……纵观整个战局,弘光朝的覆灭就是那些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风流名士们所制造的悲剧。 国亡了,家破了,西风吹尽王侯宅,光荣与尊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此词以蒜山附近为中心,将不同时代不同事件连缀一起,上下数百年,综观千古,语言精练而概括,一句一典,其景扩大,色彩黯淡。景中寓情,又因情选景,使词具有情豪气壮,悲激感人的特点,颇有苏辛之风。
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诗人在江北孤身流浪,了无乐趣。日落薄暮时分,愁思倍增。引领南望,思念起生活在京城中的友人。“乱流”以下八句,写诗人遥望江南时的所见所感。最后四句是诗人的一番想象:我在孤寂中所思念的友人,眼下正在城中与众人挥金作乐,早巳把我忘了。诗以激昂风韵,描绘了日落望江所见之乱流注壑、雾绕高林,孤鸟远翔等薄暮景象,表露了对旧友“方当得意不念旧交”的怨怼。全诗辞藻细致繁复,色彩鲜明艳丽,笔法健峭,句式多变。
一至四句,“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以平稳的交待总起全诗。
去亲为客,飘泊他乡的游子本少愉悦,今又值黄昏,感物伤怀,则更增其愁。这种情感,在鲍照以前诗人的诗文中已屡有所见,王粲《登楼赋》说:“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曹植《赠白马王彪》说:“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叹息。”皆属此类。此诗这里暗用其意,重在点明由眼前日暮而引起的思乡和怀人的忧愁,行文极其自然。
以下二句则正面写望乡,照应题目,“日落岭云归”,承接上文的“薄暮”,进一步补充说明忧思增深。白日西匿,在诗人眼中,不但有生命的鸟兽在归巢索群,甚至连无生命的云彩都在急急地回归山岭,感情又进了一层,更深切地引起了他飘泊孤独、无所归依的苦痛忧思。思乡怀人之情,至此乃跃然纸上。“延颈望江阴”,切题之“望”。“江阴”,既交待了荀丞所在之地为江南,又暗示了自己辗转飘泊于江北。延颈而望,表现了对家乡和旧友的急切思念,是上文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至十二句,正面写望江所见和感受。
“乱流灇大壑,长雾匝高林。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是望江所见的晚景:无数条水流正杂乱地向巨大的长江汇合聚拢,随着暮色的渐深,夜雾弥漫开来,环绕着两岸无边无际的高大林木,向天边绵延伸展,与落日余霞相接,浑然一体。数句写长江日暮景色,气象雄浑,同时又透出几分黯淡的色彩,和诗人当时的忧愁凄凉心境颇相融合,情在景中,耐人咀嚼。此后诗人继续写望江所见,由无生命的林木、云雾转到有生命的禽鸟,“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日落云归,暮色苍茫,鸟兽皆已回归巢穴,可此时却仍有孤鸟独飞,怆然长鸣。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连翩浮想。曹植《杂诗》之一说:“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首慕远人,愿欲托遗音。”此诗二句暗用其意,孤鸟哀鸣,犹云游子的悲鸣,都是在“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语)。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二句。“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诗人由孤鸟独飞,进而推想到和它命运类似的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旧友的无限思慕。
十三至十六句,切题之“赠荀丞”。“君居帝京内”,转入赠友正题,交待荀丞及其所居地点乃京都建康。“高会日挥金”,写荀丞的优越处境:日日置酒高会,挥金如土。元嘉末,荀万秋在京任尚书左丞,是当时执政的徐湛之一派中的重要人物,《宋书·徐湛之传》载湛之豪奢,“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荀赤松的生活,恐怕亦复如此。
结尾二句则承此而说,谓荀丞只顾自己享受,却不知道失群离居的故友,面对着江心即将沉没的一轮夕阳,正在长吁短叹呢。这二句感叹荀丞不能援手于自己,有希望得到朋友帮助之意。而态度则不卑不亢,显示了诗人人格的自尊。
此诗由日暮而引起的恋土怀乡发端,进而转到望江,又由望江的所见引至的怀乡慕友,过渡自然,层次清楚。结句“景沉”,又照应开头的“薄暮”,首尾呼应,形成整体和谐的美。暗用前人诗句而不露痕迹,含义深刻而不隐晦难读。采用比物象征手法,以独飞鸟拟孤独飘泊的游子,表现也很有形象感。此外,此诗遣词造句精炼警策,如“日落岭云归”,“乱流灇大壑,长雾匝高林”都是典型的例子,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